更多干货,请关注资产界研究中心
作者:李露
来源:金诚同达(ID:gh_116bfa8fc864)
前言
2003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没有就“重大性”进行特别规定。在2019年最高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提出“重大性要件”的概念,并明确将行政处罚作为构成“重大性”的充分条件。
但是,《九民纪要》没有进一步阐释“重大性要件”包含哪些要素。大量虚假陈述诉讼中,原告把包括虚假陈述违法行为、相关部门处罚文件、股票交易价格等各类要素都放入 “重大性要件”这一焦点下处理,被告再分别就这些要素不具有重大性进行抗辩。这显然已经跳出了《若干规定》的逻辑体系,也非《九民纪要》的本意。
实际上,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事侵权责任,法院认定赔偿责任时,仍然应当围绕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和虚假陈述纠纷的特殊要求,对“重大性要件”进行检视和论证,回归到《若干规定》的框架下。
重大性要件与法定受理条件
《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虚假陈述案件的受理条件是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在立案登记制前,这被认为是证券虚假陈述起诉的前置条件。
在立案登记制实施后,无需行政处罚决定书即可立案。随着2018年以来资本市场改革加速推进,信息披露监管与投资者保护力度加大,历史违法行为也集中爆发。特别是《九民纪要》把行政处罚作为构成重大性要件情形之一,市场反映强烈,投资者认为行政处罚从起诉的程序性条件变成了实体问题认定时的参考标准。起诉门槛降低后,虚假陈述案件数量激增。
但是,从近期生效判决和笔者代理类似案件的情况看,司法实践在该问题的认定上相对克制。在(2018)最高法民申337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428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裁定书》、(2020)辽民终1060号《民事裁定书》中,法院均认为,在《若干规定》未修订的情况下,行政处罚仍然是法院进行实体审理的前提条件。
重大性要件与侵权行为
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本质是民事侵权行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的民事侵权行为。因此,追究信披义务人的侵权赔偿责任,一方面可以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可以震慑证券违法行为,保障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九民纪要》将行政处罚作为重大性要件的一种情形,目的在于辅助法院判断已经行政处罚所涉的虚假陈述行为本身的严重性达到重大性标准。那么,可否因受到行政处罚直接推导出虚假陈述行为具有重大性这一结论?显然不妥,第一,行政处罚的法律基础是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虚假陈述行为的违法性基础是证券法律法规,两者有交集但不尽相同;第二,民事案件中,法院对于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审查,属于对侵权责任要件的认定,仍应根据《若干规定》作出实质性认定和判断。
(2020)沪民终497号《民事判决书》中,上市公司因未披露股东登记结婚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而受到行政处罚。上海金融法院指出,被行政处罚的行为并非必然构成民事侵权。实务中,还有上市公司因违反环境保护法、会计法等被行政处罚而产生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亦不能当然视为违反了证券法律规定。
实际上,重大性要件在侵权行为认定中的作用可以作反向理解。
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证监会针对违规行为有两类处理方式,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证监发[2002]31号《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体制的通知》中进行了明确区分,常见的如决定书、警示函等均属于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如果仅被证监会采取非行政性监管措施,上市公司可以抗辩其信披违规行为或虚假陈述行为不具有重大性。
同样的,证交所针对不同程度的违规行为,从轻到重,分别有纪律处分、自律监管措施和向证监会提出处罚建议三种措施。如仅受到纪律处分或者被采取自律监管措施,亦可以主张不符合重大性标准。
重大性要件与因果关系
《若干规定》对于因果关系和损失的计算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随着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从精细化审理的角度,重大性要件与因果关系这一侵权责任要件的关系最为紧密。最高院在《<九民纪要>理解与适用》中也提到,对重大性等主观性较强的事项越来越多的通过观察虚假陈述行为对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来加以证明。
具体而言,一方面,虚假陈述行为不一定对股票价格产生预期的影响,例如,诱多型的虚假陈述实施后,股票价格未上涨;或者诱空型虚假陈述后股价未下跌,可以认为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例如,(2019)渝民终346号《民事裁定书》中,重庆高院认为,北大医药公司虚假陈述的行为对外表现为控股股东减持股票,但实际仍由相关联的北大资源公司持有股票,该行为不应导致投资者积极买入股票,而应是卖出股票。至2014年10月20日,北大医药公司股价为22.58元,涨幅为68.26%,远高于同期各类指数涨幅。表明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非受代持股份事项的影响,不能证明其损失与北大医药公司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涨跌幅度相对较小,也可能被认定不具有重大性。例如(2020)最高法民申5877号《民事裁定书》中,最高院认为,尔康制药公司2015年年报中虚增营业收入和虚增净利润,分别占当期合并报表披露营业收入和披露净利润的1.03%和2.62%,该增长率同比仅增长了1.3和5.5个百分点,没有对公司业绩和重要财务指标产生实质影响。另一方面,2015年年报公布前的两个多月(自2016年1月29日至2016年4月5日期间),尔康制药公司的股价涨幅为22.26%,而该公司股票在2015年年报公布后仅上涨了2.99%,且卖出金额大于买入金额。因此,虚假记载行为未对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诱多影响。
由此可见,随着法院精细化审理虚假陈述案件的趋势,虚假陈述案件的当事人需要对证券交易价格的波动,以及侵权行为实施日、揭露日前后的证券交易量给予更多关注和论证,以证明是否符合重大性要求。
总结:重大性要件的回归
将重大性要件与证券民事侵权构成要件进行对比检视可以发现,“重大性要件”不能自成一个独立的要件体系,应当且只能放入现有证券侵权的法律逻辑体系中进行论证。即使未来对《若干规定》有所修订,证券欺诈案件也不能脱离民事侵权责任体系。司法的目的在于维护正常的资本市场秩序,既要惩治证券违法行为,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也需要包容证券市场主体正当经营行为,允许正常经营风险。
注: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资产界立场。
题图来自 Pexels,基于 CC0 协议
本文由“金诚同达”投稿资产界,并经资产界编辑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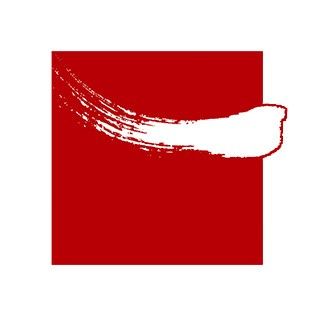 金诚同达
金诚同达 













